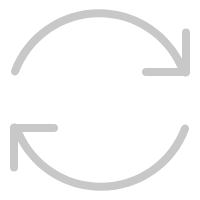

《Tumor公社》 肿瘤医学开放式媒体平台,打造肿瘤医学领域一站式解决方案,致力于为用户公众及患者提供及时、全面的肿瘤资讯、科普知识。看百科、找医生、指南分享、搭建医生与患者、患者与患者之间的桥梁,让更多人了解肿瘤、认识肿瘤、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,推动全面科学素质普及,共建肿瘤医学科普生态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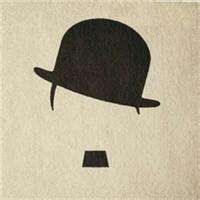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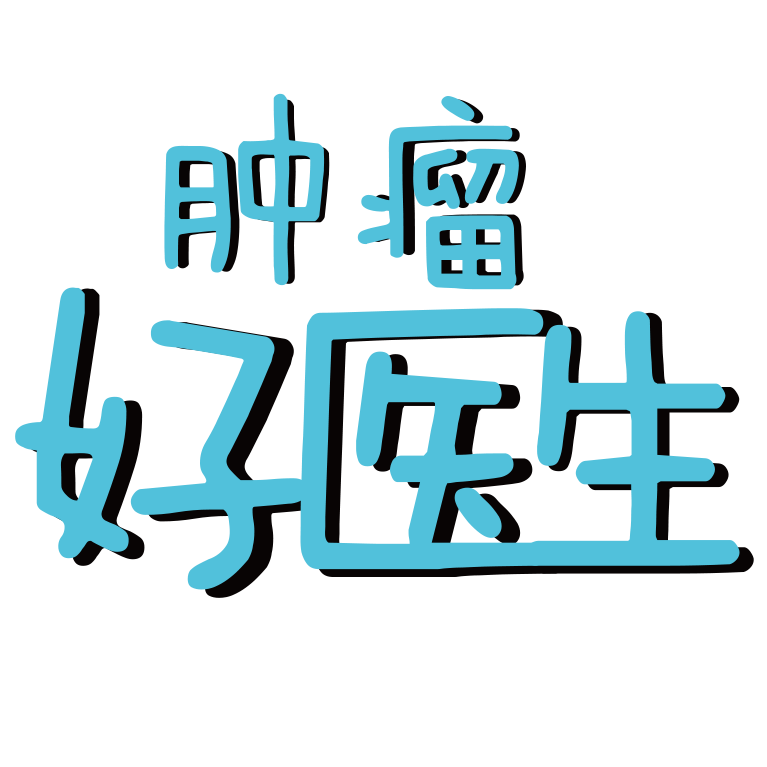
专注肿瘤专家报道,专注肿瘤人文报道,全面、细致、详实的让你了解每一位肿瘤领域大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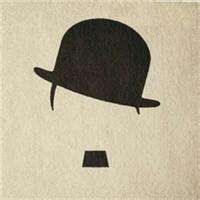
中国抗癌协会早癌筛查科普教育基地官方账号
肿瘤科女医生亲身经历记录
(以下文章是《在人间——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》后记)
在本书出版前最后的日子里,我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,小青坐在病床上与我拥抱,她化了漂亮的妆,鲜红的嘴唇看起来十分健康,她说她的病已经全好了。
我半夜醒来,给她发微信,无回应,于是联系了她的医生,也是我的朋友。医生说,很遗憾没能留住她。
小青用这种方式与我告别,我相信,她是回家了,从此再无病痛。
工作原因,我与肿瘤科医生打交道很多年,在诊室、手术室、病房旁观他们的工作,体会他们的感受,写他们的故事。当沈琳教授邀请我参与这本《在人间: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》的记录时, 我自信满满,我以为我能理解肿瘤科医生的工作,我以为我能理解癌 症患者的心情,我以为我能听懂她们对死亡的感悟……
直到遇见小青,我才知道,这一切都是骄傲的自以为是。
我和她只是2020年底在北京有短暂的交集,两个月后我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,她给我最后的语音留言,是在我梦见她的11天前发来的,听得出来她用了很大的力气,但声音依然虚弱到几乎听不清楚。她告诉我,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干枯了,整个世界也都干枯了。
我不知道“干枯”是一种什么感觉,也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——面对死亡,我是如此无知。
所以,人类的悲喜真的能相通吗?托尔斯泰在晚年的病痛中写作的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给出的答案是:不能。身患癌症的伊凡·伊里奇离开之前,亲人(他的妻子,他的子女)也无法感受到对方内心那种跌入黑洞深渊的痛苦与呻吟。杨绛先生在她 96 岁高龄所著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的自序中写道:本文,是我和自己的老、病、忙斗 争中挣扎着写成的。
说到底,衰老、疾病和死亡,都是一个人的事。
记录肿瘤科医生的故事,避不开疾病和死亡,我想,这些故事的意义,也许在于在癌症不可避免地来临时,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方向,比如如何选择适度而不浪费资源的医疗方案?如何在虚幻的期望与有品质的临终生活之间做出抉择?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 天要面对的生命课题。
说来满心惭愧,书稿的完成,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,横跨了两年多时间。李洁教授说“常常想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,结果发现越来越忙,好像越来越不会‘就好了’”,这份书稿很长时间就是这种状态。2019年8月19 日,我从北京飞到重庆,在学术会议间隙完成对程颖、 张艳桥两位教授的访谈,一周后的8月25 日,我们一家三口飞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,从此开始异国他乡的漂泊。这场迁徙历时近两年,考察、申请、安顿老人、跨国搬家、给女儿找学校、租房买车、办定居的各种手续……一路就像网游里的打怪升级,一个BOSS(怪物首领) 接着一个 BOSS,一关接着一关。
50 多个小时的录音文件趴在电脑里,从北京带到了马德里,我却似乎永远没有坐到书桌前的时间。尽管医生中没有人催我交稿,沈琳教授更是反过来安慰我“不着急,慢慢来,先把生活安排好”,但稿子拖久了就像患上某种慢性病,每时每刻侵扰着你的心,让你不得安宁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把地球上的人类都关在了家里,我也终于可以安静地坐在电脑前,治愈这场“慢性病”。
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周婷,她是沈琳院长的秘书,她一加入,出版工作就驶上了高速路。收集每一位医生的审稿意见、照片、对本书的 反馈,对接出版社各种出版事宜,各种法律文件……如果没有周婷,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定会让我的拖延症复发。周婷的敬业与责任心,让出版前的工作变得有序而高效,这本历时几年的书,终于完成了关键的最后一公里。
在此,要特别感谢周婷,也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。信任,是最让人不敢辜负的东西。
曾有人总结出女人最重要的几点:思想独立,有主见,有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;有上进心,永远不放弃自己的理想,做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,拥有快乐和成就感;经济独立,不依赖男人。
这正是这 17 位肿瘤科女医生最真实的写照,她们是中国肿瘤界最耀眼的一群女医生,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,都能独当一面;她们看过外面的世界,也遇过各种各样的人;她们独立、理性、成熟。她们也曾走过一地鸡毛的生活,一边搞临床,一边读书,一边带娃,等安顿完娃后夜深人静开始写标书、写论文,掐着各种deadline(截止时间)过日子……如今,皆已成往事,回想起来云淡风轻。
女人之间聊到深处,会不自觉放下防备,聊起成长、工作、感情、婚姻、疾病、父母、子女等等,一些只会对闺密说的隐私,就这样对我敞开,不介意把最真实的自己展露出来,而边上的录音笔一直开着。每次结束访谈后,她们都会说“不知不觉就说多了,从来没有把自己如此暴露过”。要知道,对于成熟、理性的成年人,对别人暴露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气,只有足够真诚才敢如此真实。这份真诚与信任,让我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份访谈录音,也更谨慎地对内容进行取舍。我一直认为文字如同医生的手术刀,无论对被访谈者,还是对读者,“do no harm”(不伤害)都是第一要义。
两年多前开始的访谈,我是带着许多的人生困惑在向她们寻找答案,但是两年后的今天,当初的困惑我竟然统统不记得了,是已找到了答案,还是已经放弃治疗?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想,就像“什么是幸福”这个永恒的哲学追问,也许时间本身,就是一切的答案吧。
好医生最擅于从一团乱麻中找出最重要的问题,并进行排序,尤其肿瘤内科的医生,面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各种复杂情况,他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抽丝剥茧,给出建议。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,是我对这17 位女医生进行访谈的最大收获。
人生在世,我们似乎将太多的东西揽入怀里,所以我们会不时发生崩盘,甚至引擎熄火。是信息过剩,还是行李太多?什么才是必不可缺,什么并非非有不可?这些问题,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不同的解答,因为每个人都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面对纷繁复杂、千头万绪的生活,像医生看病一样,学会取舍与排序,都是重要的能力。
让我最感动的,是沈琳教授说的“认命”,这个词,编辑曾建议改掉,我坚持原样呈现。生了病要认命,人生有缺憾也要认命,这种认命,并不是消极悲观,而是理性对待现实,改变自己能改变的,接纳自己不能改变的。
这种认命,正如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心理学家维克多·E. 弗兰克尔曾说的——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,仍然对生活说“是”。
戴志悦
2021 年 5 月 7 日